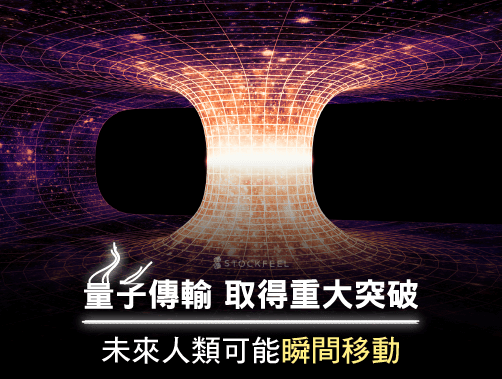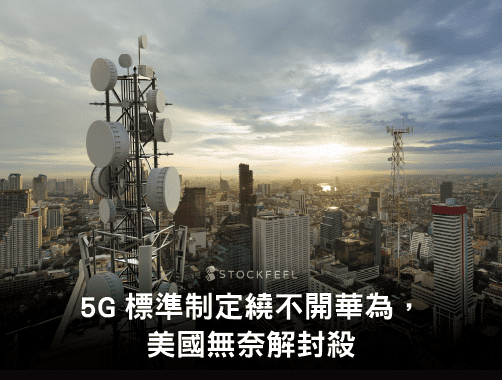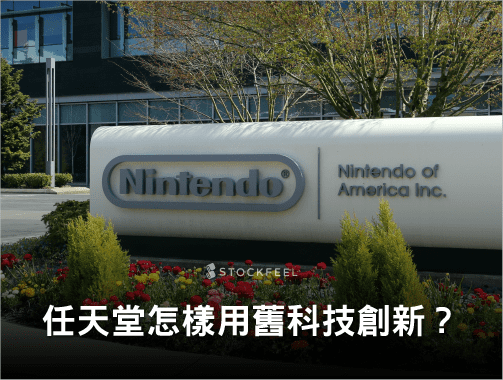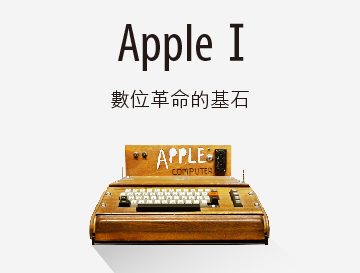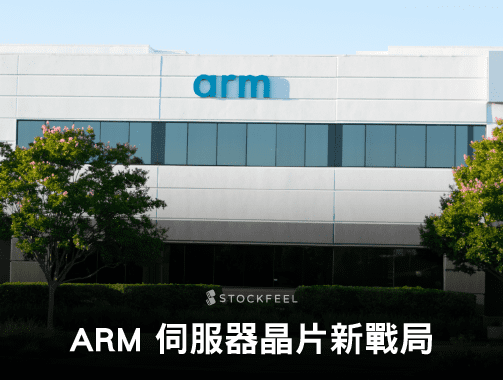台灣時間 2025 年 9 月 19 日淩晨,輝達(NVIDIA, NVDA-US)創辦人黃仁勳與英特爾(Intel, INTC-US)執行長陳立武共同召開了一場線上發表會。會上,黃仁勳宣布了一個爆炸性的消息:輝達將向老對手英特爾注資 50 億美元,並與其攜手開發革命性的「Intel x86 with RTX」晶片。
雖然黃仁勳本人只是輕描淡寫地用一句「輝達很高興成為英特爾的股東」來概括這一事件,但只要是對晶片產業有所關注的人都知道,這次晶片界兩大巨擘在歷經三十年恩怨情仇後的驚人握手,絕不會只是一場簡簡單單的交易。它不僅會震動華爾街的股市曲線,還會在全球科技圈掀起巨大的波瀾。
英特爾和輝達,一個在 PC 時代鑄就了龐大的帝國,將「Intel Inside」的印記深深植入億萬用戶的內心;另一個則在像素與幀數的洪流中崛起,用精湛的圖形處理技術點亮了虛擬世界。為了爭奪晶片市場的主導權,它們曾互為敵手二十餘年。如今它們放下恩怨,很可能會帶來整個晶片產業的一場重大洗牌。在這個節點上,重新回望雙「英」之間多年的博弈,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能理解晶片產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起初的歲月靜好
1992 年底,加州聖荷西丹尼餐廳的服務生發現,有三位年輕工程師三天、兩頭來店裡。他們點幾杯無限續杯的咖啡和便宜小菜,聊上三、四個小時。這樣的客人不算討喜,好在那位華裔總會多給些小費,才免於冷眼。
這三人正是黃仁勳、克里斯·馬拉科夫斯基( Chris Malachowsky )和柯蒂斯·普利姆(Curtis Priem)。當時,黃仁勳在 LSI Logic 公司擔任 CoreWare 部門總監(註:CoreWare 是 LSI Logic 推出的一種模組化設計框架)。他發現隨著PC普及,人們對圖形處理的需求大幅上升,而當時硬體效能卻不足,因此判斷圖形處理專用硬體將可能擁有龐大市場。同時,在太陽電腦公司從事圖形硬體開發的馬拉科夫斯基與普利姆,也看到了這個機會。三人一拍即合,決定共同創業。
1993 年 4 月,他們在丹尼餐廳寫下最初的商業計畫書,並順帶給公司取了一個奇怪的名字:Nividia。之所以選這個名字,原因頗為特別-馬拉科夫斯基和普利姆都很喜歡「嫉妒」(envy),希望自己的產品能讓對手嫉妒。於是,他們從「envy」取出「NV」的發音,生出「Nividia」這個詞,也就是後來的輝達(NVIDIA)。
創業初期,輝達資源極為匱乏。黃仁勳拜訪了許多產業巨頭,希望說服他們投資,但幾乎都被拒絕。在當時看來,GPU (圖形處理器)只是可有可無的「遊戲玩具」; PC 真正重要的是CPU (中央處理器)。各大企業幾乎押上全部賭注搶佔 CPU 市場,自然無意分心投入 GPU。
在那個時代的 CPU 市場,英特爾是絕對的王者。憑藉 x86 架構和與微軟(Microsoft, MSFT-US)的深度聯盟,英特爾幾乎壟斷 PC 處理器。就在黃仁勳等人在丹尼餐廳寫下商業計劃書的前一個月,英特爾推出了劃時代的「奔騰」 (Pentium)處理器,掀起 PC 性能新革命。統計顯示, 1993 年英特爾年營收約 88 億美元,利潤超過 20 億美元,CPU 市佔率超 80% ,一騎絕塵。相較之下,輝達才湊出 500 萬美元啟動資金,如同大象身邊的一隻螞蟻。
但正是這種巨大差距,反而為輝達創造了生存空間。身為 x86 生態的掌門人,英特爾並未封鎖這家初出茅廬的小公司,反而在平台相容性上敞開大門。 1995 年,輝達推出 NV1 晶片,儘管市場反應平平,卻在英特爾奔騰處理器生態中找到了立足之地。黃仁勳後來回憶:「英特爾沒把我們當威脅,這既是僥倖,也是機會。」
從和平滑向戰爭
1999 年,輝達推出號稱「全球首款GPU」的 GeForce 256 。這款晶片不僅震撼了遊戲玩家,也讓 PC 廠商眼前一亮。其 3D 渲染能力讓《雷神之鎚》這類遊戲從卡頓變得流暢,輝達因此聲名大噪。
那麼,面對迅速崛起的輝達,英特爾有何反應?答案是:完全沒有。在當時的決策層看來,英特爾真正關心的是 PC 產業的「地基」,也就是 CPU 市場。 GPU 的繁榮只會間接推高對 CPU 的需求。因此,輝達崛起之時,英特爾仍大方提供平台相容。戴爾(Dell, DELL-US)、惠普(HP Company, HPQ-US)等廠商紛紛將 GeForce 與英特爾平台捆綁,推向千家萬戶。
新世紀初,輝達推出 Optimus 技術,讓筆記本在英特爾整合顯示卡(iGPU)與獨立 GPU 間智慧切換,兼顧效能與續航力。這項技術成為筆記本市場的殺手鐧,惠及從學生到白領的使用者。直到此時,英特爾 CEO 安迪·格羅夫(Andy Grove)仍對輝達的崛起保持戰略默許。雖然會議上已有高層提醒他關注 GPU 市場,但這位因信奉「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著稱的 CEO,依舊以一句「GPU 是錦上添花,CPU 才是 PC 的靈魂」否決了建議。
然而,和平的表像下裂痕漸生。隨著 PC 市場爆炸性成長,晶片分工開始模糊。黃仁勳敏銳地嗅到 GPU 的潛力遠不止於遊戲。 2001 年,輝達推出 nForce 晶片組,直接挑戰英特爾晶片組業務。英特爾隨即發起專利訴訟,指控其竊取 x86 匯流排技術。
同時,英特爾也逐漸意識到 GPU 的重要性。 2004 年,英特爾啟動 Larrabee 項目,試圖打造高效能 GPU,直接挑戰 GeForce。這不僅是技術試探,更是市場覬覦。當時,PC 市場成長趨緩,單靠 CPU 難以支撐長期績效;而行動裝置和專業運算需求初現,GPU 自然成為英特爾必須爭取的關鍵賽道。
至此,雙「英」之間互不侵犯的默契終於終結。
專利戰場上的初次衝突
相較於初出茅廬的輝達,老牌巨頭英特爾在智慧財產權法上的累積要深厚得多。自從針對輝達的法律戰開啟以來,英特爾節節勝利。到 2009 年,輝達不得不以和解收場,支付 15 億美元許可費,幾乎等於當年營收的五分之一。黃仁勳在和解後苦笑著說:「這不是結束,而是新戰場的開始。」這場官司不僅掏空了輝達的腰包,更暴露了雙方的戰略分歧,英特爾視 x86 為自家後花園,任何入侵者都必須付出代價。
這場專利戰,給黃仁勳上了深刻一課:科技競爭從來不是單純的技術賽跑,而是專利、資本與權謀的綜合競爭。對在位巨頭而言,智慧財產權才是最大的護城河。像英特爾這樣的企業,憑藉先發優勢累積了大量專利;後來者若硬剛,將面臨重重阻力。相較之下,繞過巨頭盤踞的地盤,開拓新領域才是勝利之道。
此後,輝達調整策略。一方面有意避開英特爾,轉而與 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 AMD-US)合作;另一方面,加強研發揮效果度與專利掌控。工程師回憶,那幾年公司氛圍如戰時狀態,黃仁勳也常親自督戰。他激勵團隊的話很直白:「專利是武器,所以我們要造更好的槍。」
贏了官司,卻輸了市場
雖然英特爾在法律戰上確實壓了輝達一頭,但在市場上,卻沒能遏止其進擊。 2005 年,輝達以 nForce 成功,一舉拿下晶片組市場 20% 的比例,已對英特爾基本盤造成直接威脅。雖然後來靠訴訟勝利,英特爾找回一些勢頭,但輝達羽翼已成,難再驅逐。
反觀英特爾對 GPU 市場的進攻則不順。 Larrabee 專案雄心勃勃,定位「萬能晶片」,兼顧消費級圖形、通用運算和高效能運算。為此英特爾試圖以軟體取代部分硬體功能,卻忽略了硬體優化。同時,Larrabee 由獨立團隊研發,與集顯團隊分離,資源效率甚至不如專為其平台設計的第三方 GPU。 2009 年原型測試顯示,其遊戲表現僅相當於輝達中階 GPU,遠低於預期。最終, 2010 年英特爾取消該計畫。
同時,英特爾也採取迂迴策略,透過整合顯示卡蠶食 GPU 市場。既然在 CPU 領域佔據絕對優勢,那就將 GPU 功能嵌入 CPU,讓獨顯失去空間。基於此,英特爾推出 IntelHDGraphics。起初進展順利,IntelHD 很快就成為筆記本標配;更重要的是,使用者心中逐漸形成一種定勢:顯示卡應是整合的,而不必是獨立的。
然而,現實偏愛異類。輝達並未在陰影下窒息,反而牢牢抓住遊戲玩家與高階市場。隨著《魔獸世界》《決勝時刻》等 3A 遊戲大作風靡,玩家發現整合式顯示卡無法提供流暢體驗,而GeForceGTX 系列則是表現壓倒性。獨顯不僅是一塊晶片,更逐漸成為玩家的身份識別。
更重要的是,輝達與開發者和遊戲廠商建立了緊密聯繫。從 DirectX 最佳化、PhysX 實體引擎,到 CUDA 的推出,輝達建構起「軟硬結合」的完整生態。顯示卡不再只是硬體,而是通往更沈浸、更逼真的數位世界的鑰匙。
2010 年前後,格局漸明:英特爾佔據低階集顯市場,高端獨顯則屬於輝達。這是一種意外卻穩定的分工——英特爾滿足「多數用戶夠用」的需求,輝達則以「性能極致」收割利潤。根據 JonPeddieResearch 的數據,在獨顯市場,輝達市佔率長期維持在 60% 以上,而英特爾幾乎可以忽略。
由摩爾定律到黃氏定律
眾所周知,在晶片產業有一個著名的「摩爾定律」 (Moore’s Law),其核心觀點是:積體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大約每隔 18 到 24 個月會增加一倍。身為業界龍頭,英特爾長期是摩爾定律的守護者。其內部研發遵循「嘀嗒」策略-處理器微架構更新與製程升級交錯,一年製程升級,一年架構最佳化。正是在這樣的節奏下,英特爾的產品不斷更新幾乎完美契合摩爾定律的預言。
然而,從 2005 年左右開始,摩爾定律的光芒日漸黯淡。隨著電晶體縮小放緩,製程成本越來越高。在這種背景下,英特爾依舊固守「嘀嗒」策略,但被困在 10 奈米這一關鍵節點。 CPU 主頻已難以像過去那樣提升,單核心效能也逐漸逼近天花板。
同時,在矽谷另一端,黃仁勳意識到:未來運算不再依賴單核線性提速,而是透過成千上萬個「小核心」並行運算完成。這個發現,最終演化為「黃氏定律」 (Huang’s Law)。
2006 年,輝達發表 CUDA (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架構,支援平行運算。從這款 GPU 不再只是渲染遊戲的工具,而成為全新的通用運算平台。
對當時的輝達而言,這是一場豪賭。推出 CUDA,意味著它不僅要賣晶片,還要建立完整的軟體生態:編譯器、開發工具、演算法庫、開發者社區,樣樣都不能少。對於一家市值尚不足百億美元的公司,這是一場冒險的跨界。但黃仁勳堅信,這是輝達從「顯示卡廠」邁向「計算公司」的唯一道路。
很快,CUDA 的潛力開始顯現。科學研究領域率先嚐到甜頭:史丹佛的分子動力學模擬、NASA 的氣候建模、金融高頻交易,都藉助 GPU 加速實現了數量級提升。有些科學研究團隊甚至用一塊高階顯示卡完成了過去需要超級電腦叢集才能完成的任務。
反觀英特爾,Larrabee 專案的挫折使其錯失了 GPU 計算的關鍵視窗。雖然後來推出 XeonPhi 協處理器,但與輝達 GPU 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自此,雙「英」路徑徹底分叉:英特爾困在 CPU 這片日漸艱難的高地,而輝達則在 GPU 並行計算的荒野上開闢新路。 Top500 超級電腦名單的資料印證了這一轉變: 2010 年後,GPU 加速的超算數量迅速成長,美國的 Summit、Sierra 等超級電腦均採用輝達 GPU 作為核心處理器。
這是關鍵轉折點。摩爾定律的失速,標誌著 CPU 黃金時代的終結;而 CUDA 的誕生,則為GPU 插上了飛向未來的翅膀。自此,輝達長期被英特爾壓制在邊緣的挑戰者,逐漸轉變為引領新運算範式的先鋒。
AI 時代:為輝達加冕
2012 年,AI 的歷史翻開新的一頁。傑弗裡·辛頓( Geoffrey Hinton )和兩位學生——亞歷克斯·克里澤夫斯基(Alex Krizhevsky )與伊爾亞·蘇茨克維(Ilya Sutskever) ——使用兩塊輝達 GTX580 顯卡訓練出名為 AlexNet 的深度神經網路,並在 ImageNet57% ,將影像辨識率從 85% 提升至 85% 。這項成績點燃了 AI 研究的火焰,「深度學習革命」就此拉開序幕。
與此同時,晶片產業走到關鍵路口。 CPU 已難以滿足深度學習的龐大算力需求,而 GPU 的平行架構恰好契合大規模矩陣運算。自此,輝達 GPU 從遊戲玩家的利器一躍成為推動人工智慧的引擎。
黃仁勳敏銳地捕捉到這一變局,並迅速調整戰略,將 AI 置於核心位置。 2016 年,輝達推出針對科研和企業的 DGX 超級電腦,並號稱「一台 DGX 相當於一個小型資料中心」。隨後,Volta、Ampere、Hopper 等多代 GPU 架構接連問世。這些創新不僅讓輝達性能領先,也進一步鞏固了 CUDA 生態的不可替代性——讓開發者幾乎別無選擇。
資本市場反應迅猛。 2015 年,輝達市值僅 150 億美元;到 2020 年突破 3,000 億美元; 2024 年更衝上 3 兆美元,超越蘋果(Apple, AAPL-US)與微軟,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華爾街分析師稱輝達為「AI 基礎設施的唯一供應商」,其地位幾乎等同於數位經濟的「新石油公司」。
而此時英特爾卻在 AI 浪潮前亂了陣腳。 2015 年,它斥資 167 億美元收購 FPGA 廠商 Altera,試圖透過可程式邏輯元件切入 AI; 2016 年又收購新創公司 Nervana,計畫推出深度學習加速器,但專案胎死腹中,市場無迴響。 2020 年再收購 HabanaLabs,試圖補課,但開發者註意力早已被 CUDA 鎖死,努力再次失敗。
當 OpenAI 訓練 GPT- 3 模型時,其算力完全依賴輝達 V100GPU ;GPT- 4 模型則是建立在上萬張 A100 與 H100 之上。全球最前線的 AI 公司幾乎都將命運綁定在輝達的晶片體系上。儘管英特爾仍是 CPU 巨頭,但在 AI 算力戰場上,已不見這位老英雄的身影。
可以說,AI 的崛起就是一場加冕典禮。它不僅成就了輝達的輝煌,也改寫了產業權力的中心。英特爾不再是定義計算的帝國,而輝達,已成為新算力時代的代名詞。
雙「英」背後的另一隻手
如果說 AI 革命讓輝達站上舞台中央,那麼製造環節的變遷,則揭示了英特爾衰落與輝達崛起的另一面。
過去,英特爾是矽谷無可爭議的製造霸主,不僅自行設計處理器,也掌控晶圓工廠,形成所謂「整合裝置製造商」 (Integrated Device Manu facturer,以下簡稱 IDM)模式。其製程長期領先,使競爭對手在性能與能耗方面難以望其項背。摩爾定律一度幾乎等同於「英特爾定律」。
然而,到了 10 奈米節點,英特爾的光環開始黯淡。原定 2015 年量產的 10nm 製程一再延期,直至 2019 年才勉強出貨,且良率極低,嚴重打擊市場信心。更讓人唏噓的是, Intel4 工藝也接連跳票。工藝遲滯,讓昔日的王者地位蕩然無存。 2020 年,蘋果果斷棄用英特爾處理器,轉向自研 M1 晶片——這不僅是產品選擇的轉移,更像徵英特爾霸權時代的終結。
相較之下,輝達選擇了完全不同的製造道路。自始至終,它未投入巨資自建晶圓廠,而是專注於晶片設計,製造環節完全外包給台積電。憑藉這種「無廠模式」(Fabless+Foundry),輝達得以輕裝上陣,將資源集中投入架構創新與生態建構。同時,台積電憑藉著對極紫外光刻(EUV)的持續投入,逐步在先進製程上反超英特爾,成為全球無可取代的晶圓製造巨頭。
輝達與台積電的合作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共生關係。但這也帶來新的瓶頸:台積電的產能限制直接影響輝達晶片出貨。在大幅地,今天全球頂尖 AI 公司排隊等待顯示卡的場景,正是台積電與輝達產能博弈的結果。
由此可見,雙「英」命運背後始終有台積電的影子。英特爾因失去製程領先而跌落神壇,輝達則因搭上台積電的順風車而扶搖直上。可以說,台積電成了雙「英」之外,牽動它們命運的另一隻手。
從對抗走向合作
2023 年,晶片產業的天平已徹底傾斜。 AI 熱潮推動輝達 H200GPU 供不應求,市值一路飆升至 3 兆美元。身為公司創辦人,黃仁勳被冠以「矽谷新教父」的頭銜。反觀英特爾,卻深陷泥沼: 2023 財年虧損高達 70 億美元,股價幾近腰斬。儘管 CEO 帕特·格爾辛格(Pat Gelsinger)力圖振興公司,並推出頗為亮眼的 Intel4 過程,但市佔率仍持續流失至 AMD 與台積電。
在內部,英特爾裁員潮洶湧;在外部,地緣政治陰霾加劇-中美晶片戰不斷升級。雖然獲得美國《晶片與科學法案》數百億美元補貼,但這位昔日巨頭仍難以應對供應鏈斷裂。在國會聽證會上,格爾辛格無奈表示:「我們需要盟友,而非更多敵人。」
在此背景下,英特爾不得不尋求外部「輸血」。 2023 年年中,它嘗試與三星、高通(Qualcomm, QCOM-US)洽談合作,但都因策略分歧而告吹。英特爾的示弱與主動,讓黃仁勳嗅到機會。雖然輝達在 GPU 領域已不可撼動,但在 CPU 市場始終未能取得實質突破。收購 Arm 公司失敗後,它急需一個新錨點,以進一步鞏固在 x86 生態中的地位。對此黃仁勳並不避諱——在一次內部會議中,他曾說:「既然英特爾有工廠,我們有 AI 大腦——為什麼不聯手?」
同時,地緣政治變遷也催化了「雙英」合作。中東歐晶片工廠投資潮讓英特爾意識到全球化佈局的必要性;而輝達也開始擔憂過度依賴台積電帶來的風險,迫切需要美國本土的替代夥伴。在這種共同需求下,英特爾 CEO 格爾辛格主動向黃仁勳拋出橄欖枝,雙方在矽谷一家私人俱樂部會晤,商討細節。
經過半年多磋商,「雙英合璧」終於水到渠成。於是,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曾經互為瑜亮的兩大晶片巨頭,終於走到了一起。
聯盟已成,變局仍在
毫無疑問,「雙英」的攜手將為晶片江湖帶來巨大變數。但這個由最強 GPU 與最強 CPU 供應商組成的聯盟,是否能主導未來市場?從目前來看,並不確定。
事實上,當英特爾與輝達激烈廝殺時,整個產業早已悄然生變:這場對局不再只是「雙英之爭」,而是演化為「多強博弈」。
在 CPU 市場,AMD 曾長期被英特爾壓制。但自 2017 年起,這個「千年老二」強勢反彈。隨著 Zen 架構橫空出世,AMD 重新奪回主動權。銳龍(Ryzen)在消費級市場表現亮眼,霄龍(EPYC)持續蠶食英特爾高端比例。水星研究( Mercury Research )數據顯示,截至 2023 年,AMD 在 x86CPU 市場的市佔率已接近 35% ,創下二十年來新高。
在 GPU 領域,儘管 AMD 長期處於輝達陰影之下,但其押注的開源生態 ROCm 已在部分應用中對 CUDA 形成挑戰。雖然開發者遷移成本不低,但在「算力去輝達化」的呼聲下,AMD 贏得了政策傾斜和部分企業客戶。只要機會合適,它完全可能成為挑戰「雙英聯盟」的力量。
同時,專用晶片的崛起也在改變格局。隨著 AI 算力需求激增,網路巨頭開始放棄對通用GPU的依賴,轉而自研晶片。早在 2016 年,Google 推出 TPU (Tensor Processing Unit),專為深度學習打造;亞馬遜(Amazon, AMZN-US)開發Inferentia和Trainium;特斯拉(Tesla, TSLA-US)則建構Dojo超級電腦。這些專用晶片未必能全面取代輝達,但它們預示著算力版圖可能呈現「碎片化」趨勢。不同任務和企業,可能會選擇最適合自身需求的加速器,而非一味依賴GPU。
更深層的變數來自地緣政治。對半導體產業而言,地緣政治已成為無法迴避的關鍵變數。從川普政府開始,中美圍繞晶片的博弈愈演愈烈。 2022 年,拜登政府對華實施高性能 GPU 出口管制,輝達 A100 、 H100 被列入「禁運清單」,並被迫推出性能閹割版 A800 與 H800 ;英特爾則因《晶片與科學法案》被要求在美國本土擴產。這意味著,競爭已超越企業間的技術與市場博弈,演變為國家間的策略較量。 「雙英」的前路,不僅要面對同儕挑戰,也必須在地緣政治的複雜棋局中尋找立足之地。
綜合來看,晶片產業格局愈發複雜。英特爾不再是唯一的CPU霸主,輝達也未必能永遠壟斷AI 算力。這個產業唯一不變的鐵律是:沒有永恆的王者,只有永恆的更替。未來走向何方,仍是無法預判的開放命題。
結語:顛覆式創新的一個註腳
回望「雙英」三十年恩仇,英特爾與輝達的此消彼長,恰好印證了克里斯滕森的「顛覆式創新」理論。
GPU 最初只是玩家和設計師的配角,英特爾起初並未視其為威脅。然而,真正改變格局的技術往往不是從主流開始,而是從邊緣切入。隨著 3D 渲染和科學運算的發展,GPU 的平行運算優勢凸顯,並在深度學習時代迎來爆發。輝達正是在這條邊緣路徑上一步步走到產業中心。
而英特爾的遲緩,則是「創新者的窘境」的典型案例。它並非技術落後,甚至早已預見平行運算的趨勢,Larrabee 和 XeGPU 專案也野心勃勃。但它難以主動放棄利潤豐厚的 CPU 主業,轉身投入一個看似「不成熟」的新市場。克里斯滕森指出,創新失敗往往不是因為落後,而是因為成功帶來的路徑依賴。
「主流曲線與顛覆曲線交叉」的模型,正可以用來解釋 CPU 與 GPU 的力量更替。 CPU 單核心效能提升逐步放緩,而 GPU 在矩陣運算上的表現突飛猛進。 2012 年的 AlexNet 就是交叉點之一,從此運算權力由 CPU 轉向 GPU,技術範式完成切換。
這段故事至此還未終結。現今的輝達已居高位,面對光子運算、量子處理器、類腦晶片等新興技術,是否會重蹈英特爾覆轍? 「每個創新者終將成為守成者」,這正是顛覆式創新的內在循環。
因此,這不僅是兩家企業的商業傳奇,更是一種創新法則的現實演繹。它提醒企業,不應輕視邊緣市場;提醒投資人,價值遷移往往始於不被看好的技術;也提醒政策制定者,範式切換窗口期稍縱即逝。
克里斯滕森曾說,真正的挑戰不在於科技本身,而是組織能否放下眼前的利潤,轉身迎接一個不確定的未來。英特爾與輝達的故事,正為此提供了生動註解。
《虎嗅網》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